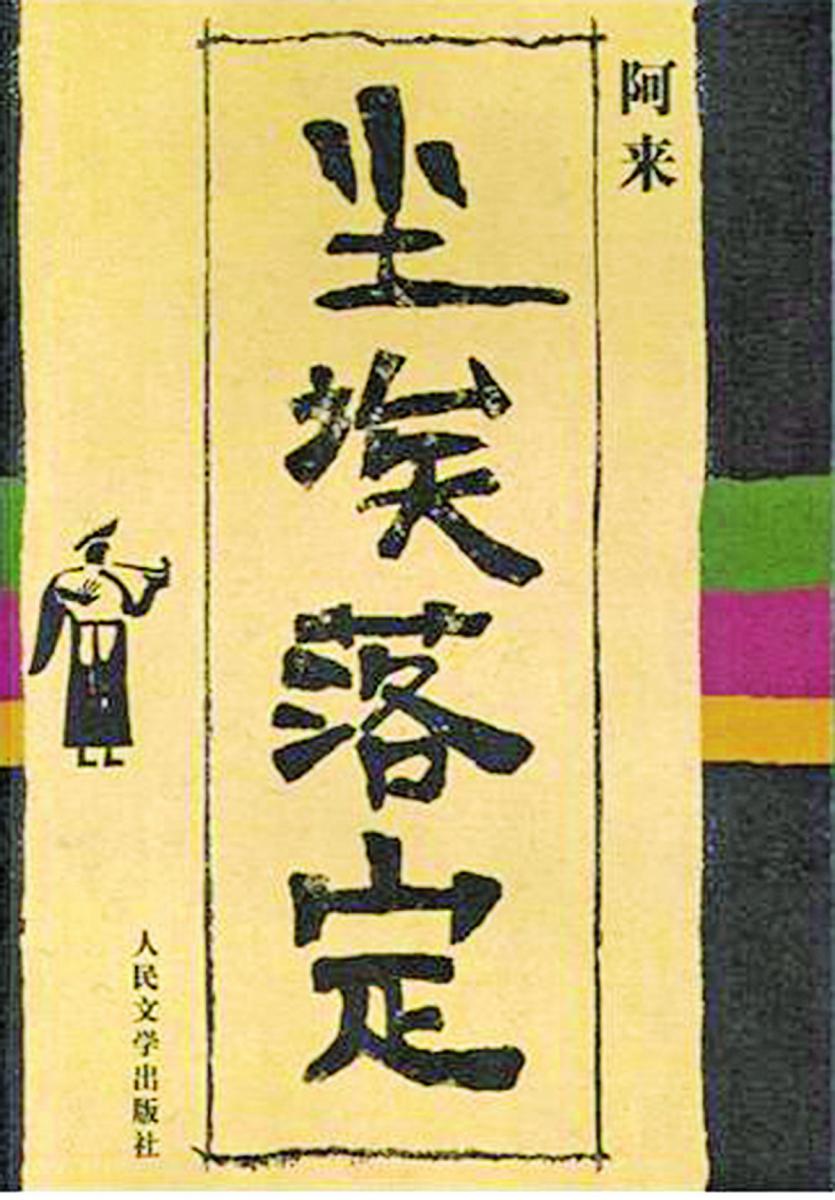身穿淡蓝色条纹衬衫,阿来神态谦和地走进大厅,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4月28日,作家阿来在广东财经大学作了题为“文学化想象下的中国边疆”的讲座,给广州高校学子带来又一场文化盛宴。随后,他接受《华南师大报》采访。
阿来似是招架不住听讲者满座后依然蜂拥而来甚至直接坐到台前的热情,在台上显得有些拘谨。但不久就恢复了幽默风趣的谈吐,笑言听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感觉总是在说另外一个人。
阿来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是藏族人。这一民族身份以及后来诸多以藏族文化风俗为背景的作品使得人们对他的认识总是先从“藏族作家”四个字开始,他的作品也被纳入“少数民族作品”。但是,阿来在演讲中选择了用中性的“边疆地带”来代替。
犹有信手拈来之势,作为例子,阿来将他的见闻像讲故事般予我们娓娓道来,故事简单却引人深思。“文学当中经常发生用文学的手段建构一种虚幻的形式”,他指出,现在很多边疆文学的写作仅仅是出于需要一些奇风异俗的目的,于是便用选择性的眼光去把边疆“浪漫化”。但是,正如阿来所感叹的:美好的期待往往容易破灭,现实往往让我们这种浪漫破产,然后我们就很轻易的转向‘妖魔化’。
谈文学的边疆问题,其实便是在谈文学的边缘化问题。细想,“不能将边疆文学边缘化”其实便是一直贯穿在阿来的演讲中:对于边疆题材的写作,既不能将其妖魔化亦不能将其浪漫化。“我们要书写一种更客观的更接近现实的东西,而不是在想象中的,”在讲座结束后的访谈中阿来这样告诉我们。阿来笔下的边疆是现实的边疆,描述的是一块真实的土地。“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恰恰“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使其作品具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
不仅是对边疆文学,阿来对现今的中国文学以及当代人面对文学的种种行为都怀有一股忧思,这无形之中成为了他的责任,我想,这是出于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担当。对于现今这个“消费社会”中把文化和文学作为一种消遣活动的理念,他表示不敢苟同。在将文学当作消遣活动的同时,文学和文化被削得越来越薄,以至于越来越多人把一切都符号化,“一谈到拉丁美洲文学就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谈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就是马尔克斯,谈到马尔克斯就是《百年孤独》。”他奉劝大家不要陷入那样的观念中去,从诗歌创作转而创作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小说,或许这是他在这一过程中所深刻领悟到的。然后,我们听到了发自肺腑的声音:“其实文学、文化本身,它能够跟几千年之间的历史互相映照,如果它只是一种休闲消遣的话,一定就不会有这么长久的生命力。”
“我觉得文学是个体的”,阿来坦言他的写作并没有什么目的或者动机,并笑称记者提到的“以前的访谈”很有可能是“二手资料”。“我就是想要通过写作找到一些东西解决一些问题”,他缓缓说道。若是想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便需要从一个点来入手折射出问题,随着写作的深入抽丝剥茧地找到根源,才能得到解决的办法,而西藏就是他所认为的这样一个点。“当我们试图描写一类人的时候,我们一个人都写不出来;但是当我们在描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恰好写出了一类人。”他引用菲茨杰拉德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在写西藏,“尽管我在写西藏,也只不过是因为上帝把生命乱空投,把我空投到西藏,而我只是熟悉这种生活而已。”
访谈临近结束,阿来和我们分享他和王安忆的一件趣事,“有一次我和王安忆去一所大学,她进去后学生一片欢呼,而我进去之后欢呼声更多,我哈哈大笑,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在意,他们认识我是因为《科幻世界》。’”
在阿来真正投入到自己的作品创作之前,写作总是藏身于他的工作间隙中零碎地进行着。他从事过很多职业,民工,乡村老师,主编……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曾任《科幻世界》的总编辑,这本杂志在他手中由一本变成五六种。“写作是我毕生所要坚持的,我终究得回归到这条道路上来,”他表示,做杂志仅仅是因为想要体验这种“商业文化”以及这其中的社会关系,“我觉得我有十年的体验了,足够了,而且至少是没有失败的吧。”
阿来终究是稳稳地回归到他的写作道路中来,他带着一支笔,游走在边疆地带,每一字一句都是身体紧贴宽厚的土地,虔诚流淌而出的情怀。